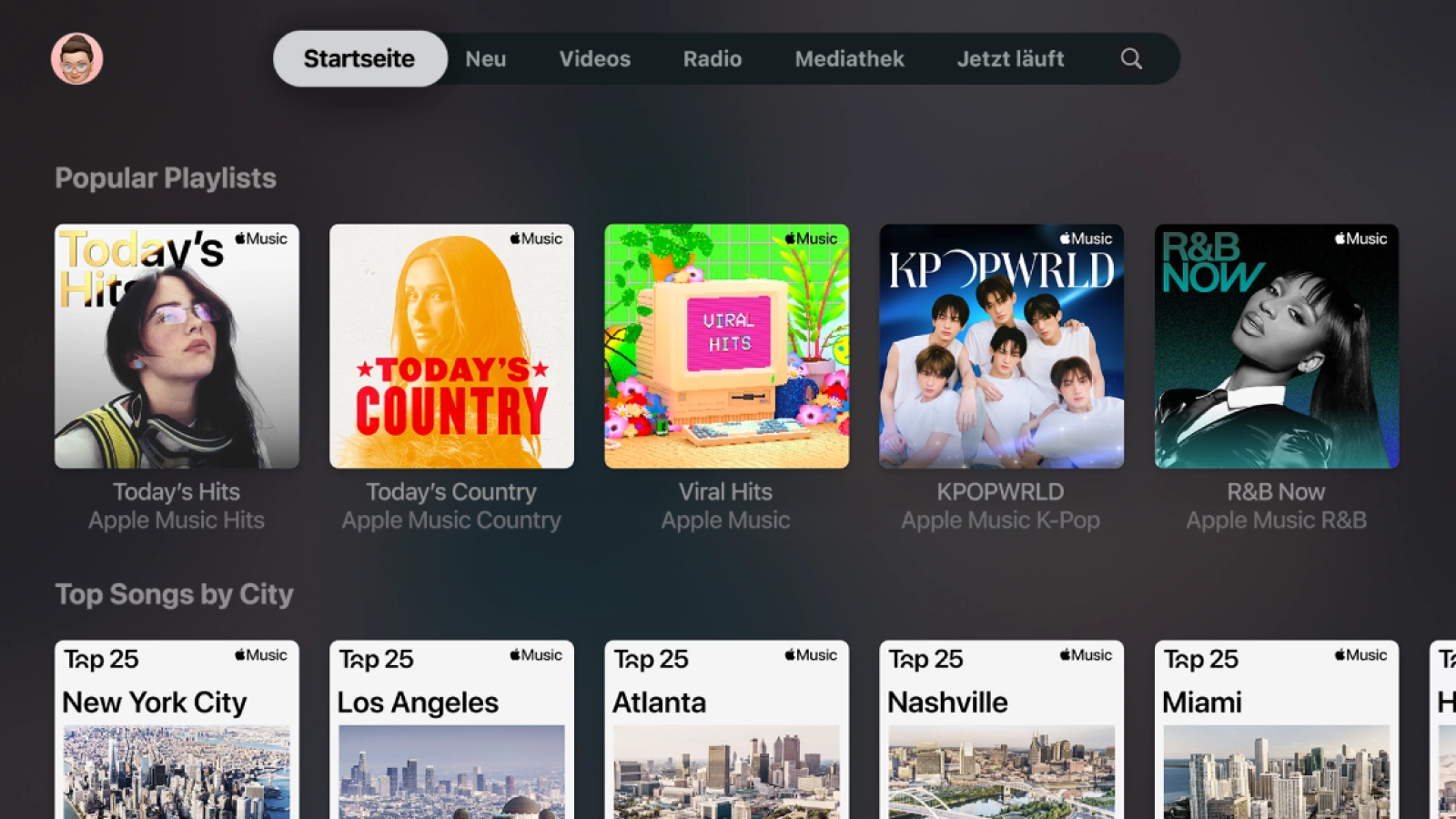本周,The Argus与作家兼电影制作人兼音乐家McKenna Blackshire’25坐下来,讨论了校园里的现场音乐场景、电影业职业生涯的影响以及成为一名艺术家意味着什么。阿格斯一家:你认为你为什么被提名为名人?McKenna Blackshire:我发了很多电子邮件!
这是我从人们那里得到的直接反应,他们本学期收到了我的一封电子邮件,内容是关于the Shed发生的一些与音乐相关的事情,或者他们看到我张贴海报。A:你能告诉我你最初是怎么加入The Shed的吗?MB:我是WESU(88.1 FM)的一名自豪的四年DJ,作为我们培训过程的一部分,我们与经验丰富的DJ一起实习,看看他们在做什么。
我和Joseph Cohen一起参加了一个节目[’22],他和他的联合主持人都很好。我记得在演出结束后凌晨3点左右,当他们开车送我们回去时,我和他们聊天,这太棒了,太独特了,只是和喜欢音乐的人聊天。几天后我遇到了他,他说:“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员,我认为你非常适合这个团体。我们在我家见面,就像,过来吧。”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场音乐的。
他们有这种做法,在喷泉大道58号(现在是我的后院)的棚屋里举办这些小型音乐会,只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,一个乐队演奏,然后他们录制下来并放在YouTube上。对于这里的许多学生乐队来说,这是一种保存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并与其他人分享的方式。
当我进来的时候,他们在奇怪的COVID〔-19〕过渡期改变和扩大了它,所以我遇到了很多很酷的人,他们知道如何设置音响设备,或者制作实验朋克音乐,或者所有这些疯狂的东西,试图在校园里制作不同类型的现场音乐展示和学生才艺。A:我没想到你现在住在有棚屋的房子里——这么圆。MB:太意外了!
我记得夏天给艾比(Abraham’23])发短信,他在我大二的时候经营着the Shed,要求我提供旧的Instagram密码。她说:“这是喷泉的某个数字,我不记得了。”我说:“我住在喷泉上的一所房子里,后院有一个棚屋。”然后我登录了Instagram,我尝试了58喷泉,它奏效了,我说,“天哪!”A:你是怎么学会英语和电影的?MB:我一直都很喜欢艺术。
我一直想以任何方式、形状或形式成为一名艺术家,但我从小就被这种身份的抽象吸引力所吸引,在一切事物之间漂浮,从未真正陷入任何困境。我试着当过一段时间的钢琴家,试过一段时期的画家,我真的很喜欢写作,而且我总是很不善于与人交谈,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。这个页面是我唯一能说出我想说的话的地方,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考虑成为一名作家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发现自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沮丧,因为我会在脑海中看到一些东西,我只想把它写在纸上,但我永远无法捕捉到它的本来面目。电影似乎是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。A:你认为在[洛杉矶]长大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吗?MB:是的,当然。我的意思是,我有点讨厌洛杉矶,既然不是被迫,我不会考虑在那里住很长时间。但有一件事真的很神奇,我一直很感激自己来自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。
接触并参与所有这些不同的艺术就像,艺术是魔法,如果你想的话,你也可以这样做。所以我来到卫斯理安,因为我知道我想学习电影,但我对去一所学校(比如纽约大学蒂施分校)非常犹豫,在那里我只能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。尽管我很喜欢它,但我不是一个善于做出重大、连贯决定的人,尤其是在17岁的时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感激现在能来到这里,因为四年后,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那么喜欢电影,或者至少是电影学校教给你的电影。
我刚才在看的这部电影中有一句话,“要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,你必须成为自己的微型资本家”,这是真的,我讨厌它。我喜欢电影,但我喜欢的所有电影都是人们不拍这样的电影,只是他们有一些需要说的话或需要讲的故事。A:没错,这就是媒介,但也许不是商业。MB:没错。去卫斯理,能够弄清楚作为一名艺术家对我意味着什么。我喜欢电影,我喜欢写作,我不知道我想在有形的身份感上做什么,但我喜欢做这些事情,我会探索它们。
这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。A:你觉得自己从大一开始就变了吗?MB:我觉得我变得不那么胆小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担心其他人,试图成为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的人。这就是我害怕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[或]作家的原因,现在仍然如此。但我慢慢意识到,做这件事的方法是无限的。我深深地被自己不是一个合适的电影系学生、英语系学生、音乐家或朋友所困扰。
然后,非常感激地,通过认识那些只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对此充满信心的人,我开始更加信任自己。我认为,在这一点上,我克服了对自己的巨大而长期的恐惧和不确定性。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充满信心的人。想想四年前,我永远不会这样评价自己,这太疯狂了。A:想想接下来的四年,或者接下来的八年。你毕业后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吗?MB:哈莱姆区朔姆堡黑人文化研究中心有一个驻留项目,这将是惊人的。
所以我正在申请这个项目,我很幸运地从我们的英语系获得了一笔拨款,在夏天做了一个关于哈莱姆艺术界的项目,我想做的和说的还有很多,但我不能,因为我要回大学了。艾灵顿[Davis’25]和我可能会一起搬到这座城市。我很想继续做音乐。无论我在哪里,我都希望身边有一台相机,试图捕捉和收集所有这些奇怪的小经历,事后看来,回首卫斯理,看看这个地方有多疯狂、特别、奇怪和棒。A:
你曾多次提到收集东西——这对你来说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吗?MB:[创意写作英语副教授Danielle Vogel前几天开始上课]说,“告诉我你作为一名作家的项目是什么。告诉我。”我说,这实际上是我需要被问到的问题。作为一名作家和艺术家,我的目标是不想忘记一些事情,我想保存一些东西。我认为这真的很讽刺,因为我肯定也是一个很快就会扔掉东西的人,或者我已经很长时间了。
我在这门课上为写作项目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关于船只的——我做船只是为了什么?这是事物、人和经历,只是我喜欢以一种非常美丽、转瞬即逝、但也非常自由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(事物)的随机组合。昨晚我在杜克节的时候,我看着人们玩耍,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跳舞、微笑和交谈。那种时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事情。然而,艺术或与人相处是我余生想做什么的关键。为了篇幅和清晰度,本次采访经过了编辑。